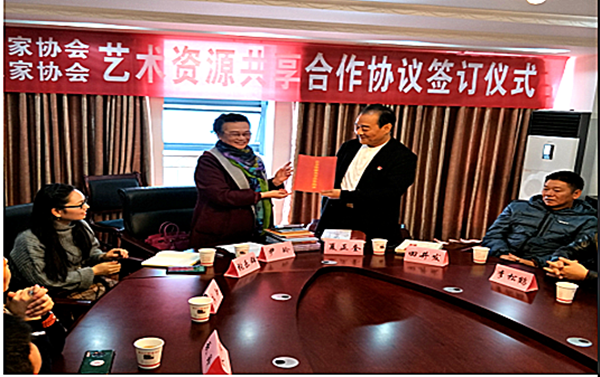儿子:回乡当“新型农民”
回乡当农民,并不是像父辈那样“刀耕火种”,而是有着更多规划
父亲:威逼断绝关系
离开农村,做一个城市人,才是成功
20年前·冲突
20年前,罗强不顾父亲反对,离开农村进城打工,父亲三年未与他联系——因为父亲希望儿子能通过读书进入城市,而不是仅仅在城市打工。好在,儿子经多年打拼在城里安家,成为一名“城里人”,父子间的多年芥蒂由此化解。
20年后·冲突
20年后,当罗强携妻带女返乡,准备当个“新型农民”时,父亲再次被激怒,坚持要分家断绝关系:“离开农村,做一个城市人,才是成功。”对此,罗强有些无奈:“人到中年愈发思乡;根在那里,朋友都在那里。”
清晨8点,炊烟还未散尽,37岁的罗强,带着一家三口已经进了村。汽车轮子碾过山间的碎石路,发出清脆的咔咔声。父亲老罗在二楼的窗边看到车来,狠狠跺了一脚,气鼓鼓地返回屋子睡下。
这是春节后,罗强和家人返乡种地最平常的一天。身体壮实的罗强穿着厚厚的劳保服和运动裤,从尾厢里拎出胶鞋麻利地换上;爱人小税换好运动装,盘起了头发;年仅六岁的女儿悠悠,也穿着粉红的小雨靴。
一切准备妥当,罗强问正在煮饭的母亲:“老汉呢?”母亲小声应道,“还在赌气的嘛。”罗强没再吭声,收拾好修剪果树的工具,出门去了。
忙完果园的修剪,回家吃早饭时,罗强还是没看到父亲。就让女儿上楼叫爷爷吃饭,孩子上了楼又跑下来:“爷爷说他不吃。”听到老伴又在楼下喊,老罗恶狠狠地回了一句:“吃你们的,我不吃。”
罗强闷头刨饭,他知道,只要他继续坚持在老家当农民,他跟父亲之间这场已经持续了三个月的“战争”,就不会结束。
城市
两代人的不同向往
罗强家所在的宜宾县喜捷镇新河村,距离县城只有20公里,开车仅20分钟。罗强说自己当年从农村到城市只用了几个小时,而从城市回到农村,却用了整整20年。
罗强出生在农民家庭,是个独生子,父母农闲时在小镇上经商,这让罗强的生活条件略好于同龄孩子。刚读初中时亲戚送他一把吉它,他爱不释手。“怀抱吉它,哼唱着BEYOND那些粤语歌曲,让我总想走出去看看大城市。”
实际上,老罗心里,也希望儿子能够离开农村成为一个城市人,但是他给儿子规划的路径不一样。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是老罗最常教育儿子的话,“只有读书,才能考上大学;只有考上大学,农村娃儿才有出路”。也因为有这样的期待,家里从来不让罗强帮忙干农活。罗父告诉记者,“就希望儿子好好读书,一定要通过读书走出农村,不然一点文化都没有,去了城市也只能打工。”
但到了初三,罗强不想读书了,叛逆的青春和流行歌曲的诱惑,加剧了他对城市的强烈向往、也就是在这一年,父子之间的矛盾接连爆发。
罗强的初中班主任蒋军告诉成都商报记者,罗强脑瓜子灵活,成绩一直靠前。“还经常给电台投稿,广播里偶尔能听到他写的诗歌和散文。”但就在初三这年,罗强已经完全没心思上学,成绩直线下降,这让他多次遭到父亲暴打,“两指宽的竹板子打断两次,这让我跟父亲的矛盾越来越深。”
远走
父子间三年没交流
初三快结束时,罗强跟父亲的隔阂越来越深,远在重庆打工的同学劝他去重庆打工。
于是,带着父亲给的考试费,罗强偷偷在宜宾北门汽车站买了车票。到重庆后,罗强给镇上一个亲戚打电话,让其给父母带个口信。“老头被气得火冒三丈,当场在电话里痛骂。”
65岁的老罗有着跟普通农民不一样的经历。“我十七岁就开始当记分员,不用干活,挣的工分跟别人一样多。”老罗对记者说,这样的经历让自己对文化特别看重。
因此,老罗把改变命运的希望全部寄托在了儿子身上。他把家里的旱地全部改种果树。“虽然更忙更累,但挣钱多点,好供娃娃读书。”
但儿子的辍学以及出走,打碎了老罗全部的希望。罗强回忆,自己远走重庆后,几乎每个月都给家里写信报平安。可是前三年,父亲从来没有给他回过信。忌惮于父亲的心结还没打开,整整三年,罗强不敢回家过年。
两三年后,罗强成为了理发师,开始自己独立开店,经济一步步殷实起来。
2008年,罗强从重庆返回宜宾,这一年春节,老罗有生以来第一次喝到了五粮液:“不怕你们笑话,我在宜宾活了几十年,宜宾就产五粮液,但我真是第一次喝。”
之后,通过两年打拼,罗强在宜宾滨江路最好的地段买了房子,也买了车,并很快结婚。这让老罗十分满意,因为小时候学习上从来没拿过第一的儿子,这次给老罗家挣了个第一,“村子里第一个买车的农民家庭。”
随着罗强事业步步走高,不但在雅安、成都、宜宾等地经管着多个工地,还开了房产中介公司,父子俩多年的隔阂逐渐消散。
思归
根在那里,朋友在那里
但2015年,像20年前一样,罗家父子之间,又爆发一场大战。
2015年,罗强开始清理转手城市里的生意,并注册成立家庭农场,还加入水果专业合作社。他筹划着,带着妻女,离开城市,回到农村,重新当回一个农民。乡下的老罗得知儿子的想法,急了:“城市里生活得好好的,为啥子要回农村?而且还是回来种地?”
对于父亲的问题,罗强一时不知从何说起。
首先,“年龄越大,越有漂泊感。”罗强告诉记者,现在人到中年,就愈发思乡,“根在那里,朋友都在那里。”罗强说,记得以前老家是个院子,五六户人,吃饭时都把碗端到院子来,和睦得像一家人。“现在的城里,大门有保安、单元有门禁、房子大铁门,看起来高大上,但我不喜欢。”
罗强说,不仅他有这种想法,和他一起在城里打拼的发小们聚会时,也时常感叹:适应了城市20年,还是水土不服,“天生没有城市的基因”。
他提到自己几年前听到的一首《鹿港小镇》,觉得简直写到了心坎里:“归不到的家园,鹿港的小镇,当年离家的年轻人。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
另外,他丝毫不避讳地说,自己在宜宾的事业,也并非父亲和乡邻看到的那般表面风光。但凡此种种,老罗不理解:“想家了,随时可以回来;城里打拼辛苦,回来种地就不辛苦?”罗强没法解释,只能不说话。
归来
没有想象的那般美好
罗母告诉记者,春节前,罗强处理完了城里的生意回到了老家,这彻底激怒了父亲,父子俩就此开始持续三个月的冷战。老罗先是不与儿子说话,后来还向派出所申请分户口单过,甚至一度威逼要断绝父子关系。
罗强试图跟父亲解释,他回乡做农民,并不是像父辈那样“刀耕火种”,他有着更大的盘算:先接手父亲的30多亩果园和苗圃,然后承包村里其他人的土地,争取在三年内把果园规模发展到300亩以上;兴建鱼塘活水养鱼,养跑山羊、跑山鸡,养糖蜂提取蜂蜜;再发展观光农业,并通过互联网把水果、蜂蜜等卖出去。
对于罗强的种种规划,老罗都摇头:“再怎么说得天花乱坠,说白了还是种地。”
另一方面,在回乡几个月里,罗强逐步发现,“农村也不是想象中的田园生活,更不是天堂。”首先,老家基础设施差,连接果园和大路的是一条机耕道,遇到下雨汽车根本无法行驶。他琢磨,就算自己把农业搬上了互联网,将来物流又怎么办?观光农业搞好了,就目前这个路,游客又怎么来?
此外,老家没有自来水和天然气,妻子和女儿回来后,一直跟他抱怨洗澡不方便。
而孩子,则是罗强必须要慎重考虑的因素。他回忆,刚回农村时,女儿根本不愿在老家住,假装肚子痛,他只好半夜带着孩子返回城里。这也让他意识到,女儿这代人,“血液里已经有了城市的基因”。
孩子的教育问题让他更加为难。“好的教育资源都集中在城市。”罗强说,开学后,他让爱人把孩子带回了城里读书。“不然,女儿的教育怎么办?”
罗强感觉有些进退不得,但他不想马上放弃,“还是再努力一把,如果发展好了,那个时候,老头也许就能理解我了”。
成都商报记者 罗敏 摄影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