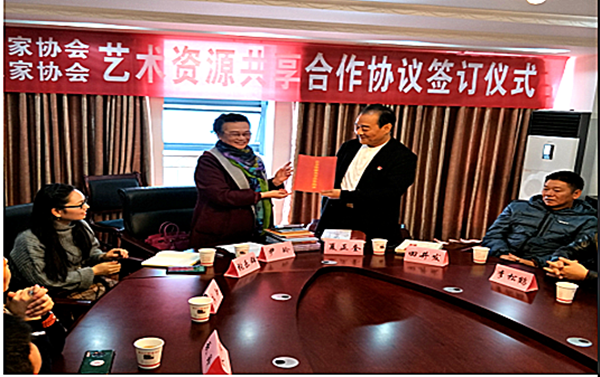◎王应槐
近几年,反映川南一带的乡村小说渐渐多了起来,给人以目不暇接之感,但大多模样相同,似曾相识,缺乏震撼人心的独特魅力。究其原因,我认为主要在两点,一是游离于现实,对人物和时代及其两者之间的关系挖掘不深,人物形象淡泊,时代感不强;二是缺乏精到的审美的发现目光,多流于一般的“乡村叙事”或者“编年史”之类,未进行深度的地域特征尤其是地域文化的描绘和彰显。正因为如此,这类乡村小说,皆为过眼云烟,在读者心中引不起半点涟漪,仅只是作者的徒劳与孤芳自赏罢了。
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中指出,作为一名优秀的作家,其小说“除了它的现实主义的真实性以外,最使我注意的是它表现了真正艺术家的勇气”。即是说,一部有影响力的小说的问世,对于作家来说,既要直面现实,也要有敢于打破常规,表现新意的勇气。邵忠奇就是这样一位作家。其中篇小说《灯魂》即如恩格斯所说的真实地反映现实,具有艺术家的勇气的作品。

这年正月,掌灯师刘彻丙在马跃庄把马马灯耍得风生水起,竟连贵州的山民都赶来看热闹。每到一处,马跃庄人都打开自家的大门,热情接待,自然赏钱也是颇为丰厚的。这一切让马跃庄的混混欧壳子看在眼里,便邀集几个哥们,也组成一支闹灯队,闹到刘彻丙的家里,与刘彻丙发生冲突,一不小心踢倒了装满竹筒花和震天雷的箩筐,刘彻丙的家顿时发生爆炸,火焰腾空,刘彻丙被炸伤,从此成为聋子和瘸子。刘彻丙的好友篾匠牛国军为讨回公理,跑到公社的后山上,举起火药枪,朝天鸣放了几枪。几年后,当时的治安员陈磊借“严打”之名,把牛国军抓进了监狱,并判死刑枪毙了。牛国军年轻的妻子王霞为此走上漫长的上诉之路。20多年以后,终于找到了老红军张将军的遗孀和子女,证明牛国军曾经帮助过红军。故事到此结束,给我们留下深沉的思考空间。

作者是把它置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这样一个社会背景之中,正如作者所描述,“今年是政策放活之后的又一个丰年,苞谷黄谷喜获丰收”。尽管大雪弥漫,但“瑞雪纷飞,奇寒的冬雪让丰年多了一份情愫,更多了一种向往与期待”。这段满含深情的文字,既表现了当时的时代特征,又充满喜悦的情绪。让我们在“瑞雪纷飞”中禁不住想起那个令人兴奋不已的年代。不啻如此。作者通过闹灯的情节,在展现中国传统文化回归的同时,反映了山民经济条件的改善,从贫困开始迈向温饱的生活,以及对精神文化的美好需求。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并未就此止步,而是勇敢地将故事向纵深发展,形象地揭示了平静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欧壳子、陈磊等阴暗猥琐的一面。而这,是我们这个社会真实的存在。若如否认或淡化了它,便是非现实主义的,或者说是伪现实主义的。

后者是马跃庄有名的篾匠,性格豪放,寡言少语,爱抽山烟、喝茶。刘彻丙耍的马马灯全都出自他的手。但当刘彻丙遭遇不公时,他敢于冲天一怒,即使被判死刑,也绝不向恶势力低头。结尾处,作者满含悲愤地写道:“刘大爷死了。他选择了牛国君的坟墓,作为自己最后的归宿,两个热爱马马灯的老头,最终聚在了一起。”更加重了人物命运的悲剧色彩,让人深思,余韵悠长。性格迥异的两个人物形象,不仅是“这一个”,也具有典型性,代表着两种不同的人物类型。这种既有个性又有共性的典型形象,特别是山乡小人物的典型,那苍凉悲壮的人生命运,以及在空旷的山野中喷发出的人性火焰,在当今乡村小说中确实不多见。
从现实主义的真实性来看,除了真实的时代感逼真的社会环境,那就是浓郁的地域文化。地域文化因地域的差异及其所处的地理条件、自然特征等,呈现出不同的审美形态。作者深入生活现场,紧紧抓住川黔交界的地域特征,从大山莽莽中发掘自古以来蕴藏着的许多鲜为人知的原始古朴的地域文化。如花灯、龙灯、狮灯、牛灯和马马灯等,跑报、武台、摔鞭、使棍、板凳龙、水火流星以及铁铧水、竹筒花、震天雷、转枝莲等等艺技。另外,与生活相关的,如喝罐儿茶、抽山烟,编制的背篼、筲箕、箩筐、鱼兜等物具。

《灯魂》的成功之处远远不止于此,它所表现的山乡小人物的命运与精神世界,尤其是那一份人性情怀,对美和善的真诚,以及在艰难困厄中对精神家园的热烈守望,时时刻刻都在拷问和鞭挞着我们社会的良心,让我们警醒,防止悲剧重演。无疑,《灯魂》在走向民族性,与人类的精神世界接轨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
2018年12月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泸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泸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
川南经济网版权与免责声明:
1、凡本网注明“来源:川南经济网”的所有作品,版权均属于川南经济网,未经本网授权,任何单位及个人不得转载、摘编或以其它方式使用上述作品。已经本网授权使用作品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并注明“来源:川南经济网”。违反上述声明者,本网将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2、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川南经济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
3、如因作品内容、版权和其它问题需要同本网联系的,请在文章发布30日内进行。
※有关作品版权事宜请联系:13882779006 邮箱:3109022@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