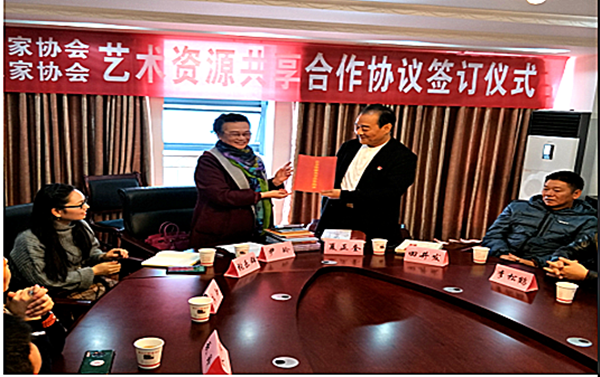作者:白连春
无论春夏秋冬,四点钟,我母亲准时醒来。穿衣,起床,上厕所,洗手,洗脸,点燃柴火,给猪煮食。猪草是头天晚上睡觉前就着月光,或者摸黑宰好的。在给猪煮食的同时,准备一家人的早饭:红苕稀饭,咸菜。红苕稀饭是用沼气煮的。锅是特制的,我二弟在城里花高价买回来的,烧开后即端起。盖严盖子,半个小时后就可以吃了。咸菜在坛子里,用筷子挟出来,拿手掰一掰,盛在碗里。然后,我母亲喂猪。一年一年,已经不知道多少年了,她都喂着十一头猪。
五点钟,我母亲出门,背着背篓,背篓里有一把镰刀,肩膀上扛着锄头,或者担着粪桶,粪桶里装着大半挑粪。如果是春天,天蒙蒙亮,如果是夏天和秋天,天已经亮了,如果是冬天,天还不亮。走三分钟,五分钟,或者十分钟,看那块地的远近,我母亲来到了地里。她先给猪割猪草。这猪草是老了的菜叶子:白菜叶子,莴笋叶子,萝卜叶子,南瓜叶子等等,还有红苕藤和青草。等她割好了猪草,无论春夏秋冬,天差不多都亮了。这天,如果她扛着锄头,她就给庄稼除一会儿草,松一会儿土,如果她担着粪,她就从地边的坑里舀点水兑在粪里,给庄稼浇灌。她这样侍候庄稼,大约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然后,她背着满满一背篓猪草,肩膀上还扛着锄头,或者担着粪桶,回家。她回到家里,我二弟和二弟媳已经起床吃了早饭,并且,双双离开了家。他们在市场上做最苦最脏最累最不挣钱的劳动:替人杀鸡和鸭子。他们的大女儿,背着书包正要出门。她看见了我母亲,说,婆,你回来了。说完,她蹦蹦跳跳地走了。
我二弟、二弟媳和他们的大女儿,他们吃过早饭后,剩余的饭菜和他们吃过的碗筷,都摆在桌子上,乱七八糟的。我母亲洗了手和脸,就着他们吃剩的饭菜,吃了属于自己的那一份早饭。这时候差不多是七点钟。我二弟和二弟媳的二女儿该起床了,我母亲来到他们的房间,抱起那孩子,给她穿衣,带她上厕所,给她洗手洗脸。然后,给她做早饭:一小碗鸡蛋面。孩子的早饭做好了,我母亲立刻喂她。她不好好吃,有时哭,有时闹,有时不想去幼儿园,有时想妈妈。喂了孩子后,我母亲牵着她,背着她,或者抱着她,把她送上已经等在村里的去幼儿园的专车。
我母亲送走孩子后,我父亲差不多起床了。他比我母亲大两岁,长年咳嗽,心脏、肺和气管都有问题,早已经不下地侍候庄稼了。一天里,他上午坐茶馆,下午唯一做的事就是帮着我母亲择第二天要卖的菜。看见我父亲起床了,我母亲赶紧给我父亲做早饭,仍然是一小碗鸡蛋面。在我父亲吃早饭的时候,我母亲担起一挑满满两箩筐菜去山下的市场卖。从我家到山下的市场,走路大约要一个小时。我母亲紧走慢走,担子一会儿从左肩换到右肩,一会儿又从右肩换到左肩,等我母亲担着菜来到市场,已经是九点钟了。我母亲的内衣,无论季节春夏秋冬,都是湿透了的。到了市场后,我母亲无法换下湿透了的内衣,就用一块毛巾,隔在背上。我母亲卖的菜从来不是一样:藤藤菜,韭菜,黄瓜,茄子,白菜,红苕,等等。她什么都准备了一些。她在地上铺一张塑料布,把菜拿出来,一一摆在塑料布上。然后,我母亲蹲在地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希望他们中的谁,在自己面前停下,买走一点自己的菜。果然,前前后后,就有那么几个人,停在了我母亲面前。我母亲赶紧站起身,对着这些停在她面前的人笑。菜是好菜,很新鲜,价钱也是便宜的。我母亲卖出了一些菜。
十点钟,收税的人来了,我母亲站起身,很不情愿地摸出两块钱。
市场上的时间过得很快,很快,就到了十一点钟了。我母亲已经饿了。菜还有一半甚至一大半没有卖。我母亲站起身,四处看了看,市场上的人不多了。大部分都是卖菜的农民。这时候,卖馒头的人来了。装着馒头的车,在市场上推来推去,叫卖声也传来传去:馒头哎五角钱一个,热腾腾香喷喷的馒头。一些卖菜的农民买了馒头,立刻大口大口地吃起来。我母亲蹲下身,偷偷地咽了一口口水,她扭开脸,不看身边吃馒头的人。就这样,我母亲坚持着自己的饿。
我母亲这样饿着,时间就慢了许多。一个农民,是个男人,就站在我母亲对面,他吃了一个馒头,还饿,就又买了一个。看着他大口大口地吃馒头,那样享受的样子,终于,我母亲也买了一个。我母亲吃了这个馒头。时间就到了十一点半了。菜还剩余一小半没有卖。我母亲把剩余的菜装回箩筐里。她担着剩余的菜,要回家了。
回家的路是上山,我母亲担着剩余的半箩筐菜,一步一步地爬着。刚吃下的一个馒头,很快就没有了。我母亲又累又饿,不仅腿软,腰也痛起来。内衣又湿透了。湿透了的内衣粘在肉上,是那样的难受。我母亲顾不得停下来歇一歇,终于,在十二点半左右赶回了家。家里没有人,桌子上摆着一家人早饭吃剩的一摊。我母亲赶紧收拾,同时,点燃柴火,给猪煮食。她把剩菜剩饭和洗碗水洗锅水,都倒进了猪食里。这时,她才想起那湿透了的内衣。她把内衣脱下来,搭在竹杆上,换上另一件。然后,她洗手洗脸,做两个人的午饭。还是红苕稀饭。菜,就从卖剩的菜里拿一样:藤藤菜,韭菜,黄瓜,茄子,白菜,等等。这中午,只有她和我父亲吃,所以,饭和菜都做得烂些。一点钟,我父亲坐了半天茶馆回来了。他回来后洗了脸和手,就开始吃午饭。在他吃饭的时候,我母亲给猪喂食。她给猪喂完了食,我父亲也吃完了午饭,我母亲就着我父亲吃剩的饭菜吃。
一点半钟,我父亲准时躺在了床上。如果是春天、秋天和冬天,我母亲又扛着锄头或者担着粪下地侍候庄稼了,如果是夏天,这时候天热得惊人,我母亲就坐在屋檐下宰猪草。猪草是她早上割回来的。她要把今天晚上和明天早上、中午的猪草,都宰出来。长年累月,她给我的二弟养着十一头猪。十一头猪要养到每一头都至少一百八十斤,需要吃多少猪草啊。我母亲曾经向我抱怨,说,她把猪养大后,我二弟卖了,从未分给她一分钱。听到我母亲这样说,我心里除了难过,便无能为力了。我母亲和我父亲,他们和我二弟住在一起,看起来是一家人,实际上是两家人,他们的户口是分开了的。平常每个月,我二弟交电费,我母亲交水费。我母亲种菜,卖得的钱归她,这钱,她要交每个月的水费,还要给父亲一些零花,我父亲每天上午坐茶馆,偶尔还在街上吃一碗面条,最重要的是,他的药费和住院费不少,一年里,他总要在乡卫生院住那么几次院。现在,国家重视农民了,虽然农民住院也能报百分之七十,但是必须自己先把钱垫付了,且这剩下的百分之三十也不是一个小数目。

五点钟,接了孩子后,我母亲在照顾孩子的同时,要忙着给猪煮食,还要做一家人的晚饭。我母亲给猪煮好食,就立刻喂猪。一家人的晚饭:红苕饭,煮好后,她把饭端起来,随即准备菜,都是卖剩的,她择好菜,洗好,从水盆里掏出来,晾干,等着我二弟和二弟媳回来。他们回来后,他们两口子炒菜。晚上这一顿饭是一家人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顿饭,一般都是我二弟炒。我二弟买了猪肉,或者鸡、鸭、鱼等肉回来。这顿还算丰硕的晚餐,天天都是八点钟吃。吃完,我二弟和二弟媳,就带着小女儿上楼,二弟媳给孩子洗澡,二弟看电视。我母亲收拾大家吃过饭后桌子上乱七八糟的一摊。
收拾好这一切,大约九点钟。月亮早就出来了,只是升得不够高。如果是春天、秋天或者冬天,我母亲就在屋檐下,就着月光宰第二天的猪草。十一头猪,都要从十几斤,养到一百八十斤,它们究竟要吃多少猪草?这些猪草,都是我母亲一镰刀一镰刀割,一背篓一背篓地背回来,然后,一菜刀一菜刀宰出来,又一锅一锅地煮好。如果是夏天,我母亲中午就宰好猪草了,这时,她就扛着锄头,或者担着粪,来到地里,侍候庄稼:给庄稼除草、松土,或者浇灌。
月亮越升越高,越升越亮,照耀着大地,照耀着长江边上,这一个一心一意侍候庄稼的七十多岁的农妇。如果是夏天,她一般要这样侍候庄稼到十二点钟,如果是夏天中最热的几天,她睡不着,会整整一个晚上都在庄稼地里。
这,就是我母亲的一天。一天又一天,组成我母亲的一年。一年又一年,组成我母亲的一生。不停地在庄稼地奔走,侍候庄稼的一生。
在我的故乡,像我母亲这样的农妇,是你数也数不清的。每一个人的母亲,都是一样的。她们都不会写自己的名字,所以不是名词。她们没有一个是美丽的和鲜艳的,所以更不是形容词。她们一直在动,直到死的那一刻,所以她们全是动词,只是动词。
我故乡的农妇,她们的一生,绝对都是在泥土里奔走滚爬的一生,在泥土里侍候庄稼的一生,在泥土里动的一生。
除了我母亲,再比如我外婆吧,她是我母亲的母亲,她九十多岁了,还牵挂着她家地里的庄稼。我的舅舅太忙,他在村庄里当文书和会计,表弟和表妹都在外地打工。一天,我外婆拄着拐杖去地里侍候庄稼,天突然下雨了,山路又小又硬又滑,且曲折,她的脚无法走回来,就坐在雨中等。有看见的人,给我母亲捎来口信。我母亲赶紧跑去,把她背了回来。
我故乡的土地,就是这样,在一代一代母亲的手和脚中,一代一代传递的。
我爱我母亲的一切。我要好好向我母亲学习,一生,做一个动词。

苦瓜诗人白连春(初旭/摄 影)
作者介绍:白连春:1965年生于四川省泸州市沙湾乡,出版诗集《逆光劳作》《被爱者》《在一棵草的根下》《一颗汉字的泪水》散文集《向生活敬礼》小说集《天有多长地有多久》。中篇小说《二十一世纪的第一天》获《中国作家》优秀作品奖,《拯救父亲》获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中篇小说类第三名。两次获四川省文学奖,两次获四川日报文学奖。
-
川南经济网版权与免责声明:
1、凡本网注明“来源:川南经济网”的所有作品,版权均属于川南经济网,未经本网授权,任何单位及个人不得转载、摘编或以其它方式使用上述作品。已经本网授权使用作品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并注明“来源:川南经济网”。违反上述声明者,本网将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2、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川南经济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
3、如因作品内容、版权和其它问题需要同本网联系的,请在文章发布30日内进行。
※有关作品版权事宜请联系:13882779006 邮箱:3109022@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