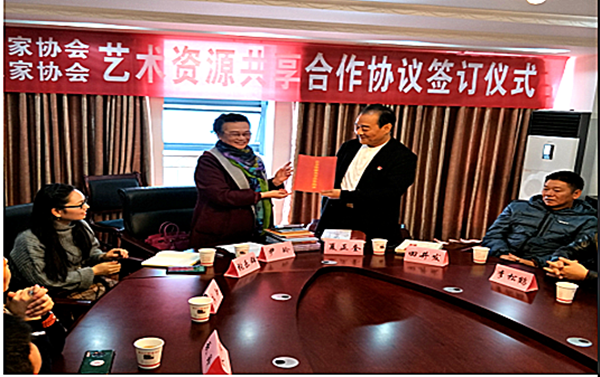作者:白连春
开始,有几块地,我母亲点了豆子。点豆子的时候,我也在。我母亲除草,挖土,打坑,我往坑里扔豆子。一个坑里扔三粒。扔好豆子后,我又往坑里盖灰。盖灰前,我还得很细致地把母亲头一年就浇好粪便的灰砸碎。拿簸箕筛,细的留下,大块的继续砸碎。直到所有的灰都从簸箕的小眼里漏下。筛好灰后,我就把灰担到母亲点豆子的地里。灰太重,装满一挑我担不动,就装大半挑,两个桶都只装一大半。我挑着大半挑灰,还得一路憩着。我将灰担到地里后,就一手一手抓起来,盖住坑里的豆子。这些灰都是浇了粪便的。抓头一把心里有点阻碍。抓了一把后心里就踏实了。就这样,我和我母亲点了五天半的豆子。我们点完了我们想点豆子的地。结果,因为天太旱,豆子发芽不好,一块地里只有稀疏的几根豆苗,有的地里甚至一根豆苗也没有。慢慢地,地里长满了草。

看见别人家长得好的豆苗,我就问母亲:人家的豆子咋个长得这么好啊?母亲回答:人家点得迟,赶上了雨。会不会是因为我们盖的是碳灰啊?家家盖的都是碳灰啊,母亲回答,现在,家家都烧蜂窝煤,只有碳灰。既然母亲这样回答,后来,再看见别人家的好豆苗,我就什么都不问了。
季节到了该栽红苕的时候了。母亲决定把我们点了豆子的地全部栽成红苕。又得除草,挖土,理杠子,红苕的苗一窝一窝都得栽在杠子里。这样,红苕才长得好。我母亲的红苕地里的红苕几乎全是我一个人栽的。我母亲除草,挖土,理杠子,我先得到埋红苕妈的地里剪红苕苗。红苕妈是提前两个月就埋好的。红苕妈是头一年留下的红苕。红苕妈在家里存放了一年,要发芽了,就把它们埋在地里,一埋在地里,它们就开始发芽,等红苕芽发到一定的时候就可以栽红苕了。这要栽的红苕苗不可过长,也不可过短,要差不多好,至于怎么样才叫差不多,我说不清楚。如果你是一个农民,你自然就知道了。红苕妈埋在地里,其中一些被老鼠咬得很烂,被老鼠吃掉一大半,它们仍然发了芽,长出的红苕苗仍然很茂盛。还有,某窝红苕苗里可能正好卧着一只癞蛤蟆。癞蛤蟆卧在红苕苗里很舒服,不愿意离开。你得把它赶走。癞蛤蟆离开后,它卧着的窝里就留下许多癞蛤蟆身上掉下来的绒毛。这些绒毛和癞蛤蟆一个颜色,它们紧紧地粘在红苕苗上。这些红苕苗本身是好的,绿油油的,你说,你是剪还是不剪这些红苕苗?犹豫一会儿,你还得剪。我就这样蹲在红苕妈地里,用剪刀剪红苕苗,剪满一背篓就背到地里。等我背了红苕苗来,我母亲在地里给地除草,挖土,理杠子已经大半块地了。我立刻就开始栽。
当我在红苕妈地里剪红苕苗,当我在我母亲除了草,挖了土,理了杠子的地里栽红苕苗,我做这些活的时候,季节已经是春末夏初,甚至是真正的夏天了,穿不住长的厚的衣服。地里的蚊子很多。这些蚊子平时很难看见人,很难咬到人。当我专心致志地做这些活,蚊子就叮上了我。往往是,半天下来,我的身上就被蚊子叮满了疙瘩。这些疙瘩当时就红了,脸上,脖子上,腿上,脚上,臂上,手上,到处都是。我母亲看见了就心疼,说,叫你不要来栽嘛你要来。我说没事。我母亲接着说,山蚊子有毒,你有病,身体没有恢复,一咬就是一个包。这么说过后,我母亲不再说话,只埋头干活。这一次,怕红苕苗晒死,我们给红苕苗浇水,太阳大的时候,我们还割草把红苕苗盖起来。这样,三五天,新栽的红苕苗就活了。
天旱,要给地里的庄稼浇水,没有水,怎么办?附近的塘里有水,承包塘的人养了鱼不让挑水,农民们要种地就得先蓄水。于是,家家户户都在每块地的地头挖坑。挖好坑后就等着天下雨。天下雨的时候,农民就到地里,把雨水引到自己挖的坑里。这样,天下几回雨,坑里装的水就差不多了。所以,人人都尽可能地把坑挖大挖深,以便多装点水。有事没事,我母亲就在地头挖坑。我回来后不久,也帮我母亲挖了几个坑。农民们不仅给山上和半山坡的地挖坑,也给山下的田挖坑。这几年,水越来越少,山下的田里也常常没有水。

在给红苕除草和牵翻红苕藤的时候,不一会儿就会看见一条虫子。虫子可能是藏在草丛中的,也可能是长在红苕藤上的,必须在除草和牵翻红苕藤的同时,把这些虫子掐死。虫子黑黑的,软软的,胖胖的,没有骨头,在地上爬,手摸到它们的那种感觉非常不好。掐第一条虫子,我犹豫了很久,因为手触到虫子的恶心感很快就传遍了整个身和心,我整个人似乎都僵住了。我咬咬牙,还是把我发现的第一条虫子掐死了。掐死了第一条虫子,再发现虫子,掐起来就得心应手了。就这样,发现一条虫子,就立刻掐死一条虫子。有的虫子身上长满了绒毛,密密麻麻的,就是著名的毛毛虫,它们都会变成美丽的蝴蝶。但是,现在它们仍然是虫子,也得把它们掐死。后来,我母亲问我:看见虫子没有?我回答看见了。我母亲接着说,要把虫子都掐死。我说我掐死了。然后我问母亲:虫子最多吃点叶子,又吃不到红苕,为什么要掐死啊?叶子吃烂了,红苕长不好,虫子繁殖得快,不掐死,过几天就一地都是虫子了。我母亲回答。这是我母亲说的原话。在写这篇短文的时候,我没有修改我母亲说的任何一个字。这样回答我之后,不久,我母亲又说,地里的蚂蚁很多,蚂蚁也要吃红苕,蚂蚁把红苕啃烂了,红苕就没有人要了,所以,过两天要打药。药打得死蚂蚁吗?我问。打得死,能打死一百种虫。我母亲说。这样说过后,我们又不再说话。我们都埋着头,各自做各自的活。我第一次知道:蚂蚁长在庄稼地里也是虫子。平常走在路上,看见一只或几只蚂蚁,我总是小心翼翼,生怕踩着它们。它们那么小,那么顽强,总是让我心生敬仰。
当空地上的红苕栽满后,农民都要给包谷地栽红苕。这时候,包谷还在地里长着,包谷都扬了花了,一些包谷已经长成,但是还没有熟,不能掰。看着地里一棒一棒的包谷,很是喜洋洋。以前,我们这里的农民不种包谷,我们种麦子和高粱。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我们不种麦子和高粱了。

我母亲说不是,所有的庄稼种好了,产量都是很高的。我母亲说高粱酿酒,现在酒厂少了。接着,我母亲又说,麦子主要人吃,人吃得了多少呢?再说了,北方的麦子比南方的好,这包谷呢,主要喂猪。
听我母亲这样说,我明白了。我惊讶于我的母亲,一个七十多岁的地道的农妇,可以把道理说得如此简单如此透彻。
包谷一棵紧挨着一棵站着。每一棵上都挂着一棒包谷。有的挂了两棒。那挂两棒的,从上往下数,第二棒肯定长得不好,因为这第二棒是后长出来的。看来不仅人,连包谷也要少生优生。包谷挨得很紧,包谷叶子就挨得更紧。栽红苕的时候,包谷地里已经长满了草。必须先把草除净,然后才能栽红苕。幸好,这包谷地里栽红苕的杠子,人在种包谷的时候就已经理好了的,不然,在栽红苕的时候再理杠子,就更麻烦了。人在包谷丛里钻来钻去,衣服又穿得不多,包谷正当壮年,叶子茂盛极了,叶子上有尖锐的毛,扎人,叶子本身也很锋利,割人。所以,在包谷地里栽红苕,不一会儿,手臂上,脸上,就被包谷叶子划伤了,那一道一道的红痕要好多天才能消散。而且,包谷地里的蚊子,一点也不比其它地里少,有包谷掩蔽和助威,蚊子咬起人来,更加方便。人还得时刻注意:别把包谷棒子碰掉了。
即使有这诸多的困难,农民们还全都在包谷地里栽了红苕。等包谷掰了,包谷杆挖了,红苕正好亮出来,那时候的红苕见风长,一天一个样。
有两天,天下雨了,我母亲和我选择了栽红苕。因为下雨栽红苕,红苕好活。还是我母亲除草,挖土,理杠子,还是我剪红苕苗,然后栽。我戴着竹笠,我母亲戴着草帽。我要戴草帽,母亲不同意,因为草帽容易湿透。我们的背上还盖着塑料布。就这样,我们下雨天在地里栽红苕。不一会儿,我们就全身都湿透了。天虽然下着雨,仍然很热。脸上有汗水,还有雨水。雨水带着汗水,或者汗水带着雨水,从头发上,从脖子上,从背上,从屁股上,滚下来,在脸上纵横驰骋,一个劲儿往眼睛里钻,弄得眼睛火辣辣地疼,却无法擦一下。我在栽红苕,两只手上都粘满了泥,根本不可能擦眼睛。擦一下脸,还勉强。为什么雨水和汗水,从头发上,从脖子上,从背上,从屁股上,都滚到脸上来了呢?因为我得时刻撅着屁股弯下腰低埋着头,这样才能栽好红苕。下雨天还刮点风,总是把塑料布刮翻了,虽然背心已经湿透,但那基本上是汗水打湿的,不是雨水。汗水打湿了不会感冒,而雨水打湿了就有可能感冒。所以塑料布刮翻了,就得伸手把它翻过来。手上有泥,很快就弄得背上都有泥了。半天红苕栽下来,我就一身都是泥。还有,下雨天栽红苕,你穿鞋也好,你不穿鞋也好,都是麻烦事。你穿鞋,很快鞋底上就粘满泥,走都走不动,必须时常拿手把鞋底上粘的泥抠掉。你不穿鞋,光着脚,地里可能有刺,有碎石片等杂物,重要的是土地肥沃,粪气很容易钻进肉里,你要长粪泡。有谁知道粪泡是什么东西吗?这种东西长在身上,使你奇痒无比,晚上睡觉发热了,更觉得奇痒。你会不住手地抠,直到抠破皮肤,抠出血,然后,挤出粪泡里的粪水,让这些粪水慢慢地淌干为止。
一个夏天,我的手和脚都长满了粪泡。现在,我写这篇短文都忍不住要抠。我没有问过母亲:你长没有长粪泡?她回答长了,我会难过。她回答没长,那是骗我。
我母亲和我,我们栽遍了我们应该栽红苕的地。而且,我们还给红苕地除了一次草,牵翻了一次红苕藤。我们再除一次草,再牵翻一次红苕藤,到了秋天,红苕就可以挖了。这中间,我母亲还得给红苕最少打一次药,浇灌一次粪。
为了保护我,这两种农活,一种危险,一种脏,我母亲绝对不让我做。
我七十多岁的母亲。

苦瓜诗人白连春(初旭/摄 影)
作者介绍:白连春:1965年生于四川省泸州市沙湾乡,出版诗集《逆光劳作》《被爱者》《在一棵草的根下》《一颗汉字的泪水》散文集《向生活敬礼》小说集《天有多长地有多久》。中篇小说《二十一世纪的第一天》获《中国作家》优秀作品奖,《拯救父亲》获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中篇小说类第三名。两次获四川省文学奖,两次获四川日报文学奖。
-
川南经济网版权与免责声明:
1、凡本网注明“来源:川南经济网”的所有作品,版权均属于川南经济网,未经本网授权,任何单位及个人不得转载、摘编或以其它方式使用上述作品。已经本网授权使用作品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并注明“来源:川南经济网”。违反上述声明者,本网将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2、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川南经济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
3、如因作品内容、版权和其它问题需要同本网联系的,请在文章发布30日内进行。
※有关作品版权事宜请联系:13882779006 邮箱:3109022@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