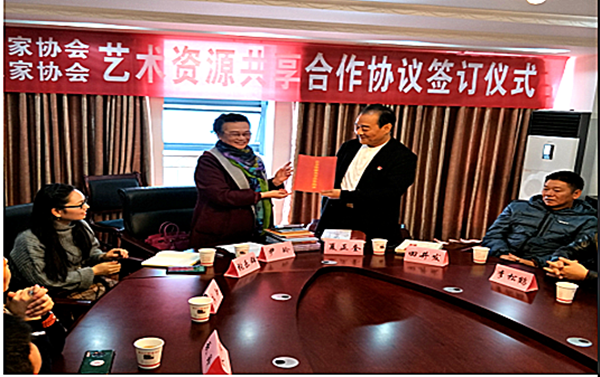作者:白连春
多年前,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我母亲种了一块地的韭菜。韭菜种下后,第二年,第三年,都用不着再种了,只管割。韭菜割了后还会再发。头一天傍晚割了,第二天早上,你到地里一看,新韭菜已经发出来了。绿油油的小脑袋,刚刚探出泥土,每一片上都顶着一颗亮晶晶的露珠,简直像一个童话,或者一个梦。
种韭菜必须管理得好,心细,每次割时,都得把泥土翻开,割后得立刻浇灌粪水,一半粪一半水这样兑着,五六天,等新韭菜长得差不多高后,又得把翻开的泥土盖上。盖泥土有技巧,只能盖住韭菜的根部。韭菜还必须除草。草尤其得除勤点,不然,韭菜本身长得极像草,草一长起来,很容易就把韭菜淹没了。韭菜一旦被草淹没,照不到阳光,通不到风,很快就会烂掉。曾经有一个著名的笑话,讽刺知识分子,说,他们分不清韭菜和麦苗。这个笑话本身就是知识分子自己编出来的。农民即使闭着眼睛,都能把韭菜和麦苗分开。韭菜是一根一根的,麦苗是一窝一窝的。它们的叶子完全不同,麦苗的叶子上有细细的绒毛,韭菜的叶子干干净净的,摸起来厚实,光洁,有弹力。还有,它们的香味也有很大的区别。麦苗的香味清纯些,韭菜的香味浓烈些。这两样东西,一种是粮食,一种是蔬菜,都是养活我们人的命的。

比如春天,就比如春节前后吧,这几天东北人爱吃饺子,需要大量的韭菜。人人都在玩耍,穿着新衣服,漂漂亮亮,走亲访友,在庆祝新的一年的到来,吃好的喝香的,想尽了一切办法让自己快乐。成群结队,许多城里人来到农村,许多农村人来到城里,相互观赏新年的好风光,大包小包地拎着:水果、糖、烟和酒,各种各样的营养品。那些背井离乡的人,基本上都回来了,手里拿着或多或少的钱,他们在故乡的田野上闹得更欢。我却必须天天都帮着我母亲择韭菜。我母亲把韭菜从地里割回家。不多,也就是十斤左右。这十斤左右的韭菜放在家门口,我就坐在家门口择韭菜。为什么要在家门口择韭菜呢?因为放在屋里,屋里没有开灯,看不清;放在屋外,又太冷。时不时,一阵冬天和春天交替的风吹来,斜斜的,吹在脸上和手上,都像刀子。如果再下点雨,那就更冷了。春雨绵绵,意思是说春天的雨多,细小,不大,但是扎实,一下下很长时间,绵绵不绝。一场雨下过三五天,是常事。一天到晚淅淅沥沥的总是下着。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指的就是这个时间段。许多地方都有初春寒的说法。所以,我母亲就把割回家的韭菜放在家门口。我坐在家门口,背朝向屋子,脸朝向外。这样,不致于让过往的风吹着腰。一个冬天和一个春天,我经常坐在我母亲家的这个位置。

这洗韭菜对于农民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我母亲从来不主动要我洗韭菜。洗韭菜成了我母亲的专业。我,因为先择了半天韭菜,到洗的时候,一开始,我不会去帮我母亲。说实话,我的手已经冻僵了。那僵劲儿还没有过来呢。等我母亲洗了不知道多久了,我才走到池塘边。我母亲会说:你别来了,快洗完了。我母亲这样说。我就不去帮她。如果我母亲什么都不说,我就必须去帮她。这么说吧,即使我帮我母亲,十斤左右的韭菜,我最多洗两斤。一,我母亲先洗了很久了,二,我洗得没有我母亲快和干净。但是,我蹲在地上,挨在我母亲身边,帮她洗韭菜,我就是只洗了一根,我母亲都是高兴的。一般情况下,我母亲坚决不要我帮她洗韭菜。一般情况下,我母亲的韭菜不是剩余太多,还有太多没洗,我也不会帮她洗韭菜。因为医生反复告诉过我和我母亲,我不能感冒,我一感冒比其他人严重,就有可能引起肺结核的复发,肺结核如果复发了,就难以治好。医生说的关于我的这一点,我母亲是牢牢地记在心里了的。

韭菜择洗干净后,第二天早上,不管风吹雨打,我母亲都要把韭菜和其它的菜一起,担到市场上去卖。在我们家,这卖菜也是我母亲的专业。以前,我父亲身体好的时候,卖菜是他的专业。我父亲卖菜和我母亲卖菜是完全不同的。我父亲卖菜,无论菜多菜少,不到中午以后,他是不回家的。他卖了菜后,总要去街边的小酒店喝酒。二两酒,或者一碟花生米,或者一小盘子猪头肉。我父亲就把自己给醉倒在路边。有时候到了下午了,天快黑了,我父亲都没有回来。那这一天,他的酒就喝多了,他肯定喝了半斤以上。他醉倒在路边,在某一片不知名的草丛里。我母亲就一路找去,终于找到了,她就把我醉了的父亲背回家。有时候,我母亲太忙,或者她连续背了几天我父亲,实在是太累了,或者,干脆,她那天不想背他了,她就要我和二弟去担他。我和我二弟,我们一个拿扁担,一个拿箩筐。找到我父亲后,就把他装进箩筐里,然后,我和我二弟一人抬一头。这事还得加上我三弟和四弟。我三弟挑着我父亲卖菜的担子。我四弟扶在箩筐边,因为箩筐太小,不能完全放下我父亲。我们兄弟四个,我们这样浩浩荡荡地把我们喝醉了的父亲抬回家。在我的少年时代,我们兄弟四个的抬父亲行动,成了我们村庄一道亮丽的风景。至今,还有人时不时地问起这件事,作为一个笑话。我父亲卖菜,他只要喝醉了,那么,他卖菜的钱,就会一分不剩。或者是他全部花完了,或者是他醉倒在路边,被别人掏走了,我不得而知。后来,我父亲的身体不好了,他担不动一挑菜了,这菜就归我母亲卖了。我母亲卖菜,总是早去早回,卖菜的钱,当然全部拿回来了。我母亲从来不乱花一分钱。

我母亲包了饺子后,剩余的韭菜还没有吃完。我母亲又把韭菜炒着吃。炒韭菜,我母亲偶尔也会放鸡蛋。她是一个鸡蛋,一盆韭菜。炒了后,韭菜还没有吃完,我母亲又把韭菜煮着吃,拌着吃,总之,想尽了一切办法吃,还是没有吃完。最后,眼看着韭菜要烂了,我母亲就把韭菜喂猪了。
这东北人为什么不爱吃韭菜了呢?一天,我母亲突然问我。
现在菜很多,再说了,那东北人也不能天天吃韭菜吧?我这样回答我母亲。
后来的某一天,我母亲就把那一块地的韭菜挖了一半。多好的韭菜啊。我母亲一边挖一边叹息着。
干脆,全部都挖了吧。我说。
还是留一半吧,我母亲说,有两个老婆婆每次都给我买韭菜,她们在市场上转着找我。
为什么转着找你?我问。
因为别的人都不卖韭菜了。我母亲说。
我母亲握着锄头,慢慢地直起腰。这样慢慢地直起腰时,她的一只手扶在腰上。她七十二岁,风吹着她已经花白了的头发。堆满皱纹的脸上,是我从未见过的复杂表情,在既不痛苦也不幸福中,有一些迷惑,还有一丝淡薄的忧伤。

苦瓜诗人白连春(初旭/摄 影)
作者介绍:白连春:1965年生于四川省泸州市沙湾乡,出版诗集《逆光劳作》《被爱者》《在一棵草的根下》《一颗汉字的泪水》散文集《向生活敬礼》小说集《天有多长地有多久》。中篇小说《二十一世纪的第一天》获《中国作家》优秀作品奖,《拯救父亲》获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中篇小说类第三名。两次获四川省文学奖,两次获四川日报文学奖。
-
川南经济网版权与免责声明:
1、凡本网注明“来源:川南经济网”的所有作品,版权均属于川南经济网,未经本网授权,任何单位及个人不得转载、摘编或以其它方式使用上述作品。已经本网授权使用作品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并注明“来源:川南经济网”。违反上述声明者,本网将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2、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川南经济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
3、如因作品内容、版权和其它问题需要同本网联系的,请在文章发布30日内进行。
※有关作品版权事宜请联系:13882779006 邮箱:3109022@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