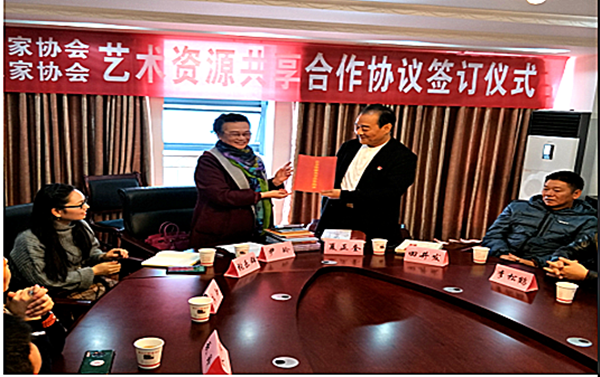作者:白连春
我出生在长江边的沙湾乡,在沙湾民办小学读的小学。每天早上,学校开门,迎面而来的就是滚滚的长江。多年前,这所小学就关门了。透过锁着的斑驳的木门,前几天傍晚,我趴在门缝向里面看了又看,里面空荡荡的,地面长满了草。那几间教室和老师的住房,已经成了危房。我的小学同学们,都像草籽一样散在风中,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扎根了。

我的初中是在泸州五中读的。泸州五中,不知道什么时候更名实验中学了。也是在长江边上。在我的小学和中学这两所学校中间,长江在这里形成一个巨大的洄水沱,每年都要淹死不少人,其中当然有学生。每到夏天,老师都要反复强调不能下河游泳。但是,总有学生下河,总有学生淹死。记忆中最深刻的一件淹死人的事,是五中的一个老师的儿子淹死了。这老师两口子都姓王,男的是泸州五中的初中数学老师,女的是沙湾公办小学的老师,他们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那年,儿子已经读大学了,放署假回来,天的确是热。一家人守在长江边,看着家里唯一的男孩下河游泳。就这样,一家人眼睁睁,看着他淹死。他是会游泳的,怎么会淹死呢?当时,河边有很多人在游泳,无论王老师一家人怎么高喊救命,没有一个人去救那孩子。据说,儿子淹死后,男王老师的头发一夜就白了,他恨自己不会游泳,在儿子即将淹死的那一刻,他没有跳进长江去救他。这王老师没有教过我。教我初中数学的是李多鉴老师。李老师的数学教得真是好。
我,一个农村孩子,和祖母相依为命,天天都有做不完的活,放学回家后从来不做作业,也不读书。我所有作业和所有书都是在课堂上赶的。就这样,每一次数学考试,我都是前三名。我热爱数学课,热爱数学老师李多鉴。李老师的老伴在老家乡下,不能来给他做饭,他经常在学校门口的小酒馆喝酒。每次看见我,他都要给我几粒花生米,或者两片猪耳朵。那时候,我几乎天天早上进城收潲水,傍晚到工厂生活区捡破烂,捡柴,或者挑粪。进进出出,都要经过泸州五中。穿越泸州五中,是我回家的唯一的路。当我挑着潲水,挑着粪,或者背着破烂,背着柴,经过学校,总免不了让老师和同学看见。他们看见我,即使不当面嘲笑我,我也自卑和羞愧得无地自容。况且,一些同学和个别老师,的确当面嘲笑过我。当冬天,我光着脚,脚上长满了冻疮,而我还不得不不挑着潲水或者粪,就是背着破烂,或者柴,我恨不得立刻死在地上。有很多次,我很晚回家,总是看见李老师坐在窗前批改作业。他的头深深地埋在一盏昏黄的灯下。那一盏灯多么温暖啊,仿佛上帝,专为我这个苦孩子的初中时代创造的天堂。

李老师长期一个人生活,年迈了,不得不和女儿女婿在一起,血压高,却爱喝酒,也许为了消除寂寞吧。后来,他中了风。我曾去医院看过他。我把李老师中风的事告诉了其他同学,但是,除了我,没有别的同学去看他。中风后,李老师仍能认出我。
我的初中语文老师,先是邓荣熙,这个去过延安的老师,头发全白了,一个人住在学校的一间小阁楼上,他的妻子是泸州二中的物理老师。泸州二中在泸州城里,是泸州市两所重点中学之一,另一所是泸州六中。邓老师和他妻子关系一直不好。每天傍晚,邓老师就着一小碟花生米一边喝酒,一边唱歌,夜深了,仍旧不睡,或者睡不着,就写诗。他的小小的房间里,地上和床上,都堆满了《诗刊》和《星星诗刊》。从小,因为贫穷,和被父母遗弃,所以自卑,我几乎不主动和人交往。一天,天快黑了,那时候我还在读小学,我背着一背篓柴,穿越五中,听到有人唱歌。我放下背篓,情不自禁地顺着歌声走去,来到一座陈旧得已经腐烂的小阁楼下,我站住,听了一会儿,摇摇晃晃地爬上小阁楼窄窄的木楼梯。呈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个满头白发的人,他的眼睛闪烁着晶莹的泪花。当我站在小阁楼的木楼梯上,他呆呆地望着我,我也呆呆地望着他。过了好久,他给我招手,示意我到他的身边。他要我吃花生米,还要我喝酒。而我对他的书,更有兴致。我随即拿一本,坐在床上,就看了起来。那是一本《星星诗刊》。之前,捡破烂我曾捡到过半本泰戈尔的诗集,散文诗,翻译作品,很多读不懂。那时候,我读《星星诗刊》,一读,就懂了。邓老师见我喜欢,说,你拿回家看吧。就这样,一本又一本,我从邓老师那里拿了很多《诗刊》和《星星诗刊》读。白天我忙,没有时间读书,夜里,怕浪费煤油,祖母不让我读书。祖母不让我读书还有一个更好的理由:怕我成为疯子。她说书读多了人要疯。我的书全都是夜里偷偷在坟地里读的。我抓很多萤火虫放在玻璃瓶里照明,没有萤火虫的季节,我就用捡破烂卖的钱买手电筒照着。以致于我的乡民都认为我真的疯了,他们说我读书给死人听。见我真的喜欢诗,邓老师也把他自己写的诗读给我听。就这样,我从邓老师那里接受了诗歌的教育。

接着邓老师,教我初中语文的是年轻的女老师毛宏智。多年后,当我和几个同学碰上,我们谈到学校的老师,我说毛宏智漂亮,他们一致反对,我说毛宏智书教得好人也好,他们又一致反对。于是,我什么也不说了,我无话可说。我默默地听他们说这个老师不好,那个老师不对。说实话,泸州五中不是重点中学,但是,的确有几个好老师。在读初中期间,我的学习不是很好,但是,因为我的家特别:只有我和祖母两个人,于是,我年年都被评为三好学生,能够拿到奖学金和助学金。这两样金每样五块钱。所以,每学期,我都能拿到十块钱。那时候,每学期交的学费才三块钱。
很顺利,我初中毕业了,升入高中。一升入高中,教我语文的就是泸州市最著名的语文老师陈德明。陈德明的丈夫李守之,当时是泸州五中的校长兼书记。没有多久,李老师调到泸州六中当校长和书记,又没有多久,陈老师也调到了六中。六中是全市最重点的中学,学生都是尖子,老师都很优秀。就这样,我和泸州语文教得最好的老师擦肩而过。陈老师不教我后,我在泸州五中读高中,读得倍受煎熬,终于,一天早上,我跳进了滚滚的长江。那年,我十四岁不到十五岁。一个少年跳长江自杀,涉及到家庭、社会和学校等方方面面,我不想多说。因为说起来,就要说到一些人的不好。现在,我已经四十多岁了。四十多岁,我只愿意记住那些对我好的人。


当陈老师张开双手紧紧地抱住我,同时,流着泪,我在她的怀里,一动也不动,一句话也没有说,可是,我在内心里,却一个劲儿喊她。我喊她:妈妈!
在陈老师教我语文的那两个月的时间里,她借《三国演义》和《红楼梦》给我看(《三国演义》我看完了,《红楼梦》我没有看完);当我肚子痛,她喂我吃药,现在,我很怀疑当时我肚子痛,是真的,还是假的;当我赖在她家不走,她留我吃饭。在我仅有的学生时代,我很多次赖在我喜欢的老师家,目的也许并不是为了吃一顿饭。当然,那时的我,也的确想吃一顿饱饭,一顿好饭。
我还在陈世晏老师家吃过饭,还在毛宏智老师家吃过饭,还在王昆老师家吃过饭,还在廖声友老师家吃过饭,还在张兴隆老师家吃过饭。不仅泸州五中的老师,多年后,当我三十多岁,已经在文化馆工作了,我还在其它学校的老师家吃过饭。我在何白李老师家吃过饭,我在王德宗老师家吃过饭,我在蒋曙晖老师家吃过饭,我在张喻老师家吃过饭,我在李添能老师家吃过饭,我在余安中老师家吃过饭,我在田正芳老师家吃过饭,我在钱代富老师家吃过饭。一一数来,泸州城里最著名的老师,我在他们家都吃过饭。
后来,我到了北京,在汪曾祺老师家吃过饭,在林斤澜老师家吃过饭,在李一信老师家吃过饭,在吴思敬老师家吃过饭,在巴彦布老师家吃过饭,在牛汉老师家吃过饭,在蔡其矫老师家吃过饭。尤其蔡老师,他八十多岁了,无法做饭,每次都领我下饭店,他点很多点心和菜,每次都剩很多,让我拿走。有几次,我还带了朋友一起去,他仍然领我们下饭店,仍然点很多点心和菜,剩下,让我拿走。不仅如此,每次吃饭,蔡老师都省下饭店提供的毛巾不用,给我,他说,拿回家涮碗吧。

陈天啸、孙祥屏夫妇

陈天啸老师挥毫泼墨
在泸州,还有一个老师家,我去吃饭也是最多。那就是王杰军老师家。你想,我在泸州生活五年,自己不做饭,天天在别人家混饭吃,我要在别人家吃多少饭?我吃饭是这样安排的:今天在陈老师家,明天就在王老师家。在王老师家,我吃饭更随便,更自在,完全如鱼得水,如苗得雨。有时候,我连早饭都不想做,一起床就到王老师家。王老师的老伴已经去买菜了。王老师在公园打了拳,刚回来。他吃过了,或者没吃,或者捧着碗正在吃,无论哪种情况,他都会立刻给我做早饭:一碗面条,卧两个荷包蛋。吃完早饭我就走,在门口,王老师给我招手,中午来啊。这时,我已经走出他家,我回头,答应哎。王老师时常肚痛,痛一阵就不痛了,医院诊为胃病。我在北京,他给我打电话,说,我的病确诊了,是肝癌,已经晚期。我傻傻地问,痛不痛?他说痛,他还说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他给我打了电话没有多久,一天夜里我睡不着,天快亮时迷迷糊糊睡着了,却梦见了王老师。到了办公室后,我立刻给泸州王老师家打电话。电话里,他儿子说,王老师去世了,就在今天早上,就是在我梦见他的时候。
陈老师和王老师先后去世后,我回到泸州,继承了几件他们的衣服和裤子。每当出远门,坐车坐船坐飞机,或者有重要的日子,我都穿上。我喜欢王老师的一条公安蓝裤子和陈老师的一件中式衣服,也是蓝色,颜色比王老师的裤子要浅一些。这么说吧,王老师的裤子是大海的蓝,陈老师的衣服是天空的蓝。
他们是这个世界最爱我的两个老师,一个死于骨癌,一个死于肝癌,我穿上他们的衣服和裤子,他们会陪在我的身边,保佑我。
活到现在,我四十多岁,因为一场大病离开北京,回到四川,回到泸州。我的祖父祖母死了,我的几个爱我的老师死了,说实话,我一点也不怕死。
我死,就是回家,就是又可以在老师身边,听老师说话,在老师家混饭吃了。

苦瓜诗人白连春(初旭/摄 影)
作者介绍:白连春:1965年生于四川省泸州市沙湾乡,出版诗集《逆光劳作》《被爱者》《在一棵草的根下》《一颗汉字的泪水》散文集《向生活敬礼》小说集《天有多长地有多久》。中篇小说《二十一世纪的第一天》获《中国作家》优秀作品奖,《拯救父亲》获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中篇小说类第三名。两次获四川省文学奖,两次获四川日报文学奖。
-
川南经济网版权与免责声明:
1、凡本网注明“来源:川南经济网”的所有作品,版权均属于川南经济网,未经本网授权,任何单位及个人不得转载、摘编或以其它方式使用上述作品。已经本网授权使用作品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并注明“来源:川南经济网”。违反上述声明者,本网将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2、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川南经济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
3、如因作品内容、版权和其它问题需要同本网联系的,请在文章发布30日内进行。
※有关作品版权事宜请联系:13882779006 邮箱:3109022@163.com